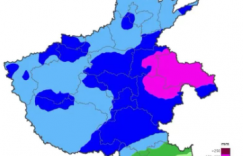【众鑫娱乐】毋庸置疑,在往后的工作和生活中,认真仔细将是我一直该秉持的人生态度。
染黑色盖白发,是所有美发项目中最简单且容易操作的。按1:1比例调配好,从发根至发尾均匀梳理即可,就算刚入行不久的学员都可轻松上手。因简便,更无需任何染发专业技巧,如今众多短发顾客,只需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染发剂都能居家自行完成。而就因这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操作,一时疏忽,让自以为拥有着丰富美发经验的我险些“大意失荆州”。

【众鑫娱乐】堂前燕子
每次去父母那里,都觉得是在过慢时光。给庭院里的绿植浇浇水,看绿萝长长的卷须拖到地上,把平安树的干叶子摘掉,细数茉莉的新芽。阳光在这些绿植的叶子上跳跃,静悄悄的,仿佛能听得到时光的脚步在轻移。

【众鑫娱乐】歌者
上世纪,在中国的大地上诞生两位音乐天才,虽然他们的名字已渐渐被人们淡忘,可他们留下的一首首脍炙人口,令人难忘的歌曲,却伟唱至今,经久不衰。 他们一个是于会冰,一个是施光南。他们才华横溢,忠于时代,为时代讴歌,他们是时代的歌者。 他们又都是短命天才,虽然结局不同,一个被社会“碾碎”,一个被时代“累倒”! 不可否认,于会泳是把现代京剧艺术推向里程碑式的人物。他一生热爱京剧,又毁于京剧,成为政治的殉葬品,将自己的生命给世人留下一缕凄远悠长的“悲声”! 音乐家不是圣人,于会泳也难免被时代所束缚,陷身政治漩涡,于会泳作品偏重政治,紧跟时代,作品充满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,表观的是革命英雄主义光辉形象。 于会泳通过对京剧艺术不断探索,古为今用,洋为中用,大胆创新,使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紧密结合,诗歌韵律的念白,将西洋乐器纳入京剧舞台,借鉴西方歌剧的舞美设计,无疑是他将现代京剧推向巅峰。 “智取威虎山”,“红灯记”,“沙家浜”,“海港”,“龙江颂”,“杜鹃山”……。成为一代人的记忆! “无产者等闲视惊涛骇浪”,“共产党时刻听从党召唤”,“党教儿做一个钢强铁汉”,“血债要用血来还”,“光辉照儿永向前”……,是责任,是担当,是忠诚,是信仰,是初心,是人类被压迫的人们向剥削阶级发出最强烈的反抗,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,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 “人民音乐家”施光南,历史上获此殊荣只有三位,另两位是聂耳与洗星海。 施光南热爱艺术,热爱时代,他的作品紧扣时代脉搏,反映的是大众心声,描绘的是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,一曲“祝酒歌”,抒发了亿万民众为共和国重获新生的喜悦,“在希望的田野上”,展现的是中国大地充满希望的勃勃生机! “请到青年队来”,“月光下的风尾竹”,“吐鲁番的葡萄熟了”,以鲜明民族音乐表现手法,去抒发革命理想主义!歌颂青春,歌颂爱情,歌颂美好的新生活! 从“打起手鼓唱起歌”,到“多情的土地”,“洁白的羽毛寄深情”……,旋律优美,振奋人心。 施光南笔耕不辍,一生创作出500多首传世之作。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是中国老百姓幸福指数最好时期,也是施光南创作的高峰期。那个时代,人心向上,社会风清气正,国民收入分配合理,年轻人的理想,就是努力完成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。 施光南为了把最美的歌声奉献给他的祖国,他的人民,终于累倒在钢琴上, 一个人的生命总是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,不可分割,时代培养音乐家,音乐家也把生命奉献给了时代! 那个时代没有“资本”,没有“利益”,那是中国人意气风发,把劳动奉献引以骄傲,引以自豪的时代。 那个时代,施光南创作“打起手鼓唱起歌”,稿费15元,创作“在希望的田野上”也只有40元! 京剧表演艺术家杨春霞说:于会泳生活习惯特别古怪,排练“杜鹃山”,整晚上的熬夜,他不上厕所,也不允许别人上厕所…… 他们是时代的歌者,更是时代的骄子。 在中国的土地上,现在不会出现,将来也不会遇有这样音乐天才!

【众鑫娱乐】瓦窑头小院渐渐恢复了静谧、甜美。
小院无风的夏夜,几只蝙蝠来回擦洗着头顶碗口大小湛蓝的天空。 姥姥挟来一卷细苇杆编就的帘子,松开上面的线绳,一甩铺展在小院中央的砖地上。取来粗布木捻单子和从小到大一直用的枕头,我脱掉身上印有碎花的裤衩子,一丝不挂地呲溜躺下去。偶尔有流星从天空划过的,我不由发出新奇的尖叫。姥姥轻摇起蒲扇,驱赶耳边哼哼吟唱的蚊虫,是惬意的夏夜。 姥姥高举蒲扇,明令喝止我的尖叫,她吓唬我喊声会惊扰蝎子、蝎子奶奶等蛰伏的昆虫倾巢而动,她一本正经地样子,让我多少年信以为真。我不满足于小院这小小的天地,提议姥姥一起去窑顶上去乘凉。姥姥扭头,分明不屑地回怼道“你那糊涂劲,夜里找不到尿盆四处乱跑,从窑顶上栽下来,小命就不保了。”唉,打小起,就跟孙悟空一样,不是想像的什么都自在,事事总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。 土胚砌筑的北房,屋檐下的土墙缝里,总有叽叽喳喳的麻雀儿,刚刚钻进去安顿下来,又常常在我的惊呼里“嗖”地飞走,不知所踪。我曾为麻雀在夜里受过我的惊扰,丢弃待哺的幼雏,而不能安居,表示些许的同情和自责。姥姥平静地说,麻雀虽小,照顾幼仔的慈爱之心,一点不比人差。单是在老祖宗流传的说法里,麻雀不思上进,不愿费力气构筑小窝,往往在小小的土墙缝里得以安身立命,辈辈如此将就下去。我真正在麻雀身上,忽然从小娃娃变成有悲悯之想的小大人了。 姥爷打着手电从外面回来,像个巡夜打更的人。我从姥爷手中接过手电筒,伸出猩红的舌头,从下巴壳照向鼻尖,转身对着姥姥扮成鬼脸,唬她。姥姥扑哧笑了,不以为然。“就这样子,大了谁会跟你?”,我打个滚,然后又拿起手电,光柱打亮房檐边早有的蛛网,一只硕大的蜘蛛由静而动,向刚刚触网又在奋力挣扎的蚊虫快速地爬去。等到各家鸡窝放下闸板,万成舅把羊牵回圈,给驴放足夜里的饲料,乘凉的人都各自回屋,大院的木门总是他最后搭起门闩。瓦窑头小院渐渐恢复了静谧、甜美。